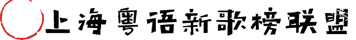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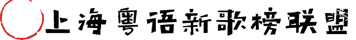
发布时间:2023-04-19 23:50:29
虎叔:各位周末好,自从上周六发了老苗(苗欣宇)的第一期“乐坛点将录”《六爷拳打丽的开影视娱乐江湖,沾叔亲写博论定乐坛三分历史》,这个内容出人意料收到很多朋友的喜欢,好多人要求连载,甚至有人发留言求征友信息……咳咳,请自重。老苗很谦虚,说写的不好,还要继续努力。今天聊的话题就是:粤语歌是怎么在香港火起来的。
难道粤语歌在香港火起来还需要原因么?当然,请听老苗细细道来,另外上一期被许冠杰骗进来的朋友,这一期终于有许冠杰了:
2002年,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把“终身成就奖”颁给了白雪仙,虽说这种奖项的得主都是功成名就、家喻户晓的老前辈,但很多资深影迷乐迷还是摸不着头脑,在骨灰级粉丝的提示下才弄明白,她就是张国荣十分喜欢的“任白”中的白雪仙,她和另一位任剑辉珠联璧合,是风云一时的粤剧名伶。
如果不是在1999年纪念任剑辉逝世十周年的活动上张国荣开腔唱过几句《帝女花》,大部分人也许这辈子都很难听到这种地方戏曲。
那个年代很多歌手都学过粤剧,唱《上海滩》的叶丽仪就是学粤剧出身,罗文后来更是唱过粤剧。张国荣的歌迷能听出他早期的唱腔有些“板”,不如后期那么随性洒脱,还以为是录音条件或者唱片监制的问题,其实,如果联想到罗文、叶丽仪那种字正腔圆的唱法,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受到粤剧粤曲唱法影响的——黄沾说,粤剧粤曲的唱法,是要把曲词每个字的首韵、腹韵和尾韵全部清楚地唱出,它和日后出现的非常注重咬字的“广告歌”,一起影响了粤语流行曲的唱法。
粤剧在上世纪50年代逐渐式微,这与香港人口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有关。
抗日战争之前,香港人口只有22万左右;,大量避难民众涌入香港,1941年的人口数字暴增为160万,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时快速下降为60万;1950年,人口数字又飞速上升为220万。显然,以上的人口数字像蹦极一样窜上窜下,是和国内局势有关。十年后的1960年,香港人口达到301万,有统计说这其中有100万的偷渡人口。1970年,香港人口接近400万,到了1979年,香港人口达到510万。
大量的外来人口除了偷渡的就是避难的,他们可能来自五湖四海,对本地的粤剧粤曲没有兴趣。在1950年前后,大上海的娱乐工业逐步搬迁到香港,姚敏、陈蝶衣等音乐创作人到香港定居,同时而来的还有白光、姚莉等歌星。这批歌星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她就是“上海滩五大歌后”之一的“电台女王”张露,也就是杜德伟的母亲——
在1996年度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好多那个时代的超级巨星集体亮相、做了颁奖嘉宾。
这样,国语流行曲进入了香港,占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半壁江山。
另外半壁江山,则是欧美流行曲。尤其是1964年Beatles巡演到香港后,迅速在年轻一代中兴起了英文歌的热潮,罗文、许冠杰、谭咏麟、林子祥都组建或参加过唱英文歌的乐队。1983年度入选第一届“香港十大劲歌金曲”的就有关正杰和黄露仪合唱的《常在我心间》,这首歌其实就是猫王的《Always on My Mind》,在那一代听惯了欧美流行乐的港人心中,虽然是填了新词,但曲调却是耳熟能详的,所以,《常在我心间》很有人缘地获得了这一届的“季选最受欢迎奖”。
资深的歌迷尚能知道关正杰是谁,但对黄露仪实在陌生。
黄露仪就是黄莺莺
其实,这个名字在那个时代已经非常红了,1979年黄露仪的英文专辑就获得香港唱片业协会的金唱片奖,日后她的英文唱片竟然超越了外国歌手,在台湾创出外语唱片发行纪录。对很多不习惯听外语歌的歌迷来说,唱英文歌的黄露仪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恐怕没有人不知道1987年的《雪在烧》——
1990年的《哭砂》——
许冠杰、黄莺莺这样的老牌唱匠都是唱英文歌起家的,这至少可以说明,香港粤语流行音乐在起步时就很艰难。但是,变化很快就来了。这种文化上的变化也是必然要来的,因为在香港人口暴增的背后,香港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大转型。
仔细分析一下香港人口数字,我们就能发现另一个问题:1979年香港人是510万,除去罗文这样的100万偷渡客,还剩410万,而1950年的人口则是220万。
这意味着什么呢?
很简单,1979年比1950年多出来的人口,除去经偷渡途径外来的,剩下的都是生出来的,其中偷渡客们也在生孩子。
我们看另一个让人吃惊的数据:有统计表明,1979年时,香港20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总人口的39%。
社会人口的构成不仅影响经济,还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香港粤语流行音乐的发展繁荣,也会与香港的人口结构产生关联,这些香港婴儿潮数据说明:当时香港人口总量中处于中坚位置的青少年群体,与父辈甚至个别爷爷辈的偷渡、避难不同,他们是纯正的香港生人。
很多学者曾经分析说,这一代香港人在迫切地寻找着属于香港本地的文化,寻找着自己的声音,由此粤语流行音乐开始了起步。
这些人年轻、活跃、富有激情,又占了社会总人口的四成,他们像鲶鱼一样在多元(比如国语歌与英文歌)的香港文化中窜来窜去,必然会迅速填平以往香港社会各种外来文化之间的沟壑,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批年轻人要做的不是“找”一个并不存在的本地文化,而是由他们作为主力军“创造”本地文化。
很快,本地文化的声音唱响了。1974年,也就是“我系我”时代的第一年,“无线”投拍电视剧《啼笑因缘》。在以往的很多年里,电视剧有主题曲,但没有主题歌。《啼笑因缘》的编导是王晶的父亲、老戏骨王天林,他想弄出一首主题歌来,于是找到了作曲人顾嘉辉。
顾嘉辉
当时,王天林和顾嘉辉希望用粤语填词,创作一支粤语歌曲。填词人很好找,著名的粤剧编剧、曾经和白雪仙合作整理《帝女花》唱片版本的叶绍德自然是不二人选。可演唱者让他们犯了难,担心观众不能接受“老土”的粤语歌。选来选去,他们选中了仙杜拉。
仙杜拉
仙杜拉是个中英混血儿,有人说她本名叫梁玉姬,曾与一位高山族的歌手阿美娜(Amina)成立过女子组合“The Chopsticks”,通常被称为“筷子姐妹花”(虎注:难道是筷子兄弟前身?),主要演唱欧美流行曲,但这个组合在1973年就解散了。选择仙杜拉的理由是她以前唱英文歌,而且衣着打扮非常前卫,用这种“洋化”的歌手搞一搞平衡,别让观众们骂就算不错。
这或多或少说明了当时的音乐人对粤语流行歌没有信心,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首歌马上流行了起来。
同一年,许冠杰的《鬼马双星》也红到爆棚,新一代的香港年轻人迅速认同了香港本土的音乐文化,这两首歌也奠定了粤语流行歌曲的文化地位。(待续,下周六见)
✿ 如果你对本文作者感兴趣,那么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购买他的新书《光辉岁月,不说再见》,下周六见。
该书得到香港朋友的盛赞,有图为证:
Copyright © 上海粤语新歌榜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