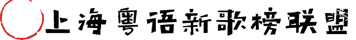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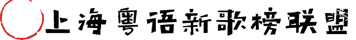
发布时间:2023-04-19 23:50:29
▲ 点击蓝字订阅新京报人物
推荐语:这是一个让记者本人都觉得“难讲”的故事。乞讨——每一个人都再熟悉不过,甚至并无好感的街头活动。
但也恰是一位父亲“耀眼”的战斗史。黄亚乌全家的经历曾触动一批志愿者纷纷加入,在志愿者四散后,他又回归一个人的战斗。
即使在广东多地将地中海贫血症(简称地贫)纳入医保的当下,仍有地贫家庭面临类似的困境。
乞讨的故事广州人并不陌生,但黄亚乌“坚持”了3年,并且仍在继续。资料图
文|袁小兵
►夜幕下,黄亚乌踩着三轮车,疲惫地穿行在街巷中。乞讨筹款已3年,连他自己也怀疑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怎样讲述这个故事是个难题,因为3年来它每天都在发生,广州人并不陌生。2006年起,4个家庭带着患有地中海贫血症(简称地贫)的孩子沿街乞讨,他们各住在一辆窄小的三轮车上,外面挂着“救救孩子!”的字幅。人们曾经为此惊讶和伤心,媒体也不吝关注。
但如果3年后,只剩下这个叫黄亚乌的男子还在率领妻儿站立街头,不仅媒体已经疲劳,人们疑窦渐生,连他自己也在怀疑还能坚持多久。
这是个关于“坚持”的故事。志愿者们坚持帮他唱了1年歌,为儿子筹够了钱,但儿子还是死了,志愿者们先后离开。为挽救同样患有地贫的女儿,黄亚乌坚持从一个说话结巴、羞涩的乡下男人变成嗓音低沉的流浪歌手。妻子坚持第五次怀孕,期望通过这个危险的小生命来救他的姐姐。
举家乞讨志愿者们来了
九两银终于在2007年1月13日的27岁生日下定决心。3天后,他抱着吉他来到岗顶人行天桥下黄亚乌的三轮车前,“一开始了就收不住了”。、阿怀、阿虎……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他们的口号是“坚持坚持再坚持”。
每10个广东人就有1个是轻型地贫患者。这是一种遗传性溶血性血液病,多发生在地中海国家、中东、亚洲以及我国的广西、广东、海南。这些患者与常人无异,但如果两个患者结婚,孩子则有25%几率染上重型地贫,每月需花费几千元输血和排出体内的铁,根治则需要20万-40万元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而且手术风险较高。
不幸的是,同为轻型地贫患者的黄亚乌和妻子吴少云,生下的两个孩子都是重型地贫患儿。他们居住在远离珠三角的揭阳市惠来县鳌江镇溪头村,对地贫一无所知,也没有医生对他们进行过这方面的婚检、孕检和产检。
黄亚乌说:“2001年晓敏出生,1个月后就脸色青黄,经常拉肚子,拖到5个月后去镇医院抽血,那不叫血,黄的比红的还多,但直到她一周岁去汕头检查时,才得知是重型地贫。这时晓明在肚子里4个月,医生没有说也应该对他检查。结果,他生下来后和姐姐一样。”
家里只有3亩农田,加上打散工全家月收入不足千元。“人家都叫我把孩子丢弃掉,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但我不能不要他们,我一直坚持着。如果两个孩子死了,我也活不下去。”吴少云说。2003年发现怀上第三个孩子后,她做了人流手术,因为家里无力生养。
2006年3月,夫妻俩再也坚持不住,抱着两个孩子去广州乞讨,把病情写在一张纸上,旁边是南方医院的证明,但每天只能讨到几十元钱。
此时,来自梅州的地贫患儿小文炬和父母住在一辆流动的三轮车上,歌手江湖等人在帮他们义演,8个月就凑够了25万元。中秋节那天,黄亚乌效仿着把全家搬进一辆同样大小的三轮车。50多岁的父母也从乡下过来,住在另一辆三轮车上乞讨。
为了医治患病的子女,黄亚乌举家在广州街头乞讨。资料图
九两银,广州电信行业的录音师,80后网络歌手,喜欢把牛仔裤脚塞进高帮皮靴,长长的银色腰链垂挂到大腿,经常变化的夸张发型让人感觉是个愤怒青年,但他说他其实是个感性、温和的人。
2006年9月在街头见到黄亚乌一家时,他刚做父亲不久,“自己的孩子病了都心疼得想哭,而黄大哥却要面对2个孩子的生死。他妻子和他妈妈拉着我的手,哭着说让我帮他们唱歌,我当时也哭了,但我没有立即答应,因为我也有孩子、家庭、工作,自身有顾虑。”
“但是经过几次探访,每次都感动一次、震撼一次。”九两银终于在2007年1月13日的27岁生日下定决心。3天后,他抱着吉他来到岗顶人行天桥下黄亚乌的三轮车前,第一次义演他没有唱很多,因为为了壮胆他带来了很多朋友,大家都争着献唱,4个小时里小木箱里就有了800多元。
“我先不管以后能坚持多久,我先做发起人。”九两银这么想,他也和黄亚乌说好,一周义演两个晚上,但“一开始了就收不住了”。“看到捐款在增多,希望在增加,我恨不得有空的时候就去,连上班午休时间都想去,后来就一周去4次,从下午到晚上。”
、阿怀、阿虎、小白、老关、小莫、冯大小姐、星仔……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有的唱歌,有的在一旁向路人呼吁,江湖有时也从小文炬身边赶来。九两银还从教会拉来朋友,他们共同信仰“施比受更有福”,现在志愿者们的口号则是:“坚持坚持再坚持!”
比实际年龄更显老成的阿虎说:“繁华都市我们离爱心越来越远,其实大家内心都很善良,只是没有机会和勇气去表达。比如有些同事和客户好几次惊讶地问起,我看到你在义演哦,我就需要给他们解释,有时人会因此觉得难为情,但他们听了以后都很支持我。”
住在岗顶附近的阿怀,每天早上上班经过这里都给姐弟俩带来鸡蛋,晚上有时还从家里煲好汤送来。她是一个工作不久的快乐女孩,不忌讳在众人面前笑嘻嘻地捏着志愿者男孩的脸蛋,也会当众哭得稀里哗啦,因为这天她妈妈路过时发现她在为乞讨者呼吁,责骂她有辱门风。
一个周六,她对着话筒又哭了,对路人说她刚得知外婆摔伤了,但不能第一时间去看望,需要在这里为孩子多筹一些钱。她在QQ空间里写道:“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会放弃的!希望你们终有一天会理解我。”
外地大四女生李婵来广州找工作,没有亲友投靠,白天碰上的多是冷漠的面试官或骗子,晚上则在这个流动的志愿者群体寻求信任和温暖。她说永远忘不了一名中年妇女的回眸一笑,她把1000元钱塞进小木箱就走了。李婵是最认真的呼吁者,而且打动了捐款的一对男女,最终成为他们公司的一名员工。
九两银在电脑城的网友“回忆”好几次把他老总拉来,发现“老总很害羞,每次都匆匆而过,但是每次都有捐钱”。一个叫黄亚莉的女士先是捐了50元,还发动小区居民捐了5000元。
我在2007年4月1日黄昏来到这里,很多打工仔背着廉价皮包正坐在路边,疲倦而专注地听九两银唱歌,久久没有离去。潮阳的吴贵波刚来广州时就被骗了200元“押金”,他说路边招工启事全是骗人的,但他相信面前的九两银,“这么有才艺的人怎么可能是骗子呢?”一个戴眼镜的胖乎乎女孩则说,她更爱听歌,歌声让她觉得世界澄静,倒不太在意这个贫困家庭的情况。
城管和警察对他们网开一面,偶尔过来干涉一下,因为听歌人太多,人流几乎堵塞。一天晚上,两名警察彬彬有礼地对他们说,“希望9点后把音响调小点,因为楼上居民报警几次了,我们都不忍心赶你们。”
志愿者们给黄亚乌带来超级人气,致使捐款远超从前,最多一天有3800元。同时,志愿者们从中也得到快乐和友谊。阿虎说,他和九两银很快就成为了哥们,“在一起什么都能说,单纯、真实,和生意朋友完全不同。”
九两银也说:“这种友谊是一辈子的。”他专门写了一首歌,让阿虎、、老关和他4个人一起唱,类似《真心英雄》那种。
华南农大毕业生陈木华用DV记录下了这些故事。镜头前,晓明在歌声中踩着“吱吱呀呀”作响的童鞋,与姐姐绕着三轮车奔跑嬉戏。一个稍大点的胖男孩一直瞪大眼睛看着,这些画面从未在他生活里出现,以至于他显得目瞪口呆。
起初,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义演,帮助黄亚乌筹集治疗费用。资料图
晓明走了志愿者们也走了
晓敏的手术费用还不够,黄亚乌开始从一个“连话都说不好”的羞涩乡下男人变身为嗓音低沉的街头歌手。他一个人在战斗“就怕3分钟热度。”在2007年4月1日晚餐后的讨论中,志愿者阿韦这样提出。
他是一名挺拔的东北男孩,聊天时他说起曾接纳一名14岁的流浪女孩,后与之同居,但现在这女孩再次失踪,他天天出来寻找,孤独迷茫中就加入了义演。他口才出众,感情充沛,常唱谭咏麟的粤语歌《一生最爱》,其中一句高音“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被他演绎得“如痴如醉”。
但4天后,他却最先做了逃兵,,说是发短信,再未归来。志愿者们却没有留下他任何身份信息和照片。多日后阿韦在类似故事中被抓,,上面说“2008年5月1日保证归还手机”,但阿韦至今没有做到。
志愿者们承认受到此事打击,但核心成员没有一个退出,并开始审核新来同伴的身份证和工作单位,挡住了不少骗子。
进入7月,广州高温,持续半年的义演募捐出现明显颓势,捐款减少至不足以前的一半,有天甚至只有几十元。志愿者从4月初的近10人减至九两银孤零零一个人,这让他很痛苦。
一天深夜他在网上写道:“感觉压力好大,信心也倍受打击,连以前坚持每次义演后写日记的习惯也渐渐淡了下来……跌到了低谷状态,有点力不从心了。”
这年10月,黄亚乌一家和父母骑着三轮车来到深圳乞讨,黄亚乌在热闹的华强北,父母在蛇口。媒体报道后,深圳大学70多名学生为他义演,筹得善款2441.4元。一名叫黄波的职业指导老师特意把他们请回广州,包下一间国际会议室进行千人演讲,筹来5000多元,加上平时讲课所得1万元,全都送给黄亚乌。黄亚乌此时已筹得35万元,但只够一个孩子的治疗费用。
2008年1月,黄亚乌和父母返回广州。这时,阿怀已被公司派去黄埔,李婵去了江苏,老关有一半时间出差在外,九两银在忙着换工种,。
3月,九两银从录音师转为市场营销人员,负责粤东片的电信增值业务。热心于在网上发帖呼吁的妻子,也带着孩子回到揭阳老家经商,九两银的生活开始从广州转移出来。“这个年代做音乐很难,只能作为爱好,我需要多赚钱,缓解家庭压力。”
5月底,晓明终于找到配型骨髓,住进了南方医院。老关、阿虎和几名大学生还在坚持义演。但手术20多天后传来消息,晓明走了。
“所有志愿者受到沉重打击,有时我都在自责,如果我们不筹那么多钱,不怀那么高希望,不做这个手术,仅仅每月输血,对孩子也许是最好结果。晓明的死,有时让我突然觉得付出那么多原来是没有价值的。”九两银说。
晓敏这年已长到7岁,手术最佳时期就要过去,但她父亲手里只有10万元。
志愿者们没有回到他们身边,黄亚乌开始从一个有点口吃,被妻子嗔作“连话都说不好”的羞涩乡下男人变身成嗓音低沉的街头歌手。
他从没进过歌厅,也谈不上喜欢K歌,但他有这方面的天赋(说责任可能更恰切)。,回家(后来他们在城中村租了个小房间)就对着DVD里的歌曲练习发音。众人面前,他还懂得手抚胸口以示深情,身子会时不时地轻微摆动。一天,他听到了一个路过女孩的惊叹:“哇塞,大哥,你唱得好好听哦!”
黄亚乌一个人在战斗。
他父母在三轮车上住了近2年,每个周日清早,父亲就去教堂为孩子们祈祷,母亲则天天念着“菩萨保佑”,失去孙子后他们回到了乡下。
阿怀现在是一家出口物流报关公司的老板,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才睡,“公司离岗顶不远,没有再去义演,不是激情退去,是真没有时间。”电话里她用词谨慎,声音疲惫,没有2年前的轻快笑声。
老关继续在云浮、肇庆、广州三地行走,为公司和自己的前途殚精竭虑。,回到内蒙古老家父母身边,除了业余继续做音乐外,他还开了一家礼仪公司,“经常回忆起那段志愿者时光,挺好。”
当志愿者们跟随时代和梦想一路前行,黄亚乌还停留原地,除了失去一个孩子,生活没有任何改观。隔几个月,九两银、阿虎会请他吃饭,和他聊天;两人有时路过那里,为曾经的岁月相视一笑。
阿怀在他去深圳乞讨前赶到出租屋,塞给他200元钱,为不能继续帮助他表示歉意。那个曾经的超级气场不复存在,“坚持坚持再坚持”的口号成为一些志愿者心底的隐痛,但黄亚乌说,他对他们只有感激“他们已经比所有人做得都好。”
除了失去一个孩子,黄亚乌的生活没有任何改观。资料图
没有晓明的日子
晓明躺在无菌病房里央求爸爸:“我好饿,你煮点粥给我吃吧!”爸爸只是无助看着他拉了一晚上的肚子,母亲两次去找值班医生,医生说:“是这样子的!”第二天,爸爸给他洗了个澡,医生来了,但他还是死了。
6月21日,夏至,广州最高温36.7摄氏度,黄亚乌在烈日烘烤下和下水道涌上的臭气中又唱了一天。晚上8点,他穿过迷宫般的石牌村小巷回到出租屋。
这天是晓明离去一周年忌日,但夫妻俩不提这个,也没有任何纪念仪式。晓明走后不久,吴少云肚子里的第四个孩子被检测出仍是重型地贫儿,只好绝望地把他打掉。他们原指望这个孩子能健康生出,然后用脐带血救治晓敏,而不是用排斥性较大的他人骨髓,虽然这个配型的成功几率也只有25%。
黄亚乌说:“小孩已经有了头和手脚,先要让他死在肚子里,然后生下来,阿云受不了,住了7天院,出院后马上就做家务,因为我还要在外面唱歌。”
“每天心情不好,想起晓明,怎么白白就没了?他走的时候,我都没敢看最后一眼。”荧光灯下,吴少云坐在低矮的床上看着地面。“以前吃了那么多苦,睡在三轮车上,好冷的风啊,阿乌为了让我们睡宽点,有时睡在冰冷的地上。我用木板隔成一圈,给两个孩子洗澡。尽管苦,可一家四口都在,希望还在,一心就想着早点筹到钱,别这样生活了。但现在少了晓明,变成了一家三口,我就觉得好空,好迷茫。”
“没有晓明,家里好静,好寂寞。”4天后,我再次登门,吴少云又不断说起儿子,“他这个人好斗,家里来人,他一边跟你拉扯,一边嘻嘻哈哈和你玩,他爸爸说,晓明说话笑死人了。”
这时,她的眼圈又红了,说晓明曾是多么的乖,每天在屋子里很闷,想出去玩又怕被骂,晚饭后他就故意问:“吃完饭要干什么啊?”但她没有心情出门,就唬他:“在家看电视!”现在想来,吴少云总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后悔没有好好陪他玩,没有给他煮好吃的,没有送他去幼儿园,“他喜欢写字,读书肯定聪明。”
无法对儿子补偿,去年秋天她就把晓敏送进幼儿园,她的年龄只能读大班,居然赶上了班上的学习进度,但没有弟弟相陪,她的脾气变得急躁,常用连声尖叫表示抗议或引起他人注意。
而且,她也注意到疾病带给她和同学们的不同。有时她问妈妈:为什么我没有同学们跑得快?打响指没有他们打得响?为什么同学们都说我的手又黑又丑?
这天晚上,晓敏照例坐在床上凉席上写作业,9个算术题做对了7个。她身后窗玻璃上留着曾经租客的“唐兴华到此一住”和一些励志抒情短句,墙壁上是他们张贴的一张巨大彩画,一对近乎全裸男女拥抱在一起亲热。“这个对孩子不好,”黄亚乌皱着眉头说“但我不敢撕掉,怕房东骂。”
晓敏不管这些,她在这张彩画上贴上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许多图案,然后又撕掉。她的另一个乐趣是用彩笔在白纸上画一个五边形花朵,叫爸爸沿线剪下,中间贴一个公仔图,然后再画一个花朵……爸爸动作慢了,她就高声尖叫。
晓敏每个月要花3000多元输血和注射去铁氨。这天也轮到注射时间。她又尖叫起来,从床上跳到屋角,抓打着爸爸不让他靠近。最后她呜咽一声,听天由命般静靠在床边让爸爸打针。
这让妈妈又想起了晓明,“晓明打针时也会哭,但会求爸爸:‘你打轻点,我数到10,你再打好吗?’姐姐也学他,但现在弟弟不在,她也忘了。”
吴少云的腹部正在隆起,这是第五个小生命,也是她和丈夫为挽救晓敏而发起的另一轮抗争。道路充满凶险。6月25日,医生从她肚子里抽取羊水,最初宣布这是个轻型地贫儿,可以生育和抽取脐带血,让夫妻俩喜不自禁;但几天后,医生又说,由于羊水里渗入了少许母亲的血,还有5%的可能是重型地贫。现在,夫妻俩还在煎熬中等待第二次检测结果。
黄亚乌说,只要不是重型地贫儿,比什么都重要。在他劝告下,封闭在屋子里的吴少云开始坚持晚饭后散步,带上晓敏。
黄亚乌的坚忍让志愿者感慨。阿虎说,他原来是帮他,现在是佩服他———“一个懂得珍惜和承担,具有非常勇气的人”,“正在教我怎样做一个男人和一名父亲。”
女儿晓敏在出租屋的床上写作业,身后是一幅非常“少儿不宜”的大彩画,但爸爸不敢撕掉,“怕房东骂”。图片来自《南方都市报》
他总是示弱
强大的父亲和示弱的男人,总是在黄亚乌身上交织。
除了不敢揭下出租屋里那张少儿不宜的彩画,黄亚乌在街头更示弱。他不敢与热心的已婚女士合影,怕引起对方老公误会惹上不必要麻烦。他对城管言听计从,陪笑脸,说好话,甚至不惜下跪,只求一个唱歌的位置。
一名志愿者在日记里写到,一名城管(可能是协管)看到有女志愿者在就会“撩”她们说话,使劲拧两个孩子的脸蛋,常往小木箱里瞅,有人捐多点,他就哇哇大叫:“你们这样唱半天相当我一个月的工资!”他有时要黄亚乌给他买水喝,拿整币过来换零钱,却多要几张零钞。黄亚乌都默默承受着,也没对记者们讲起。
随着在岗顶收入的减少,黄亚乌开始辗转各地,,广州大道,江南西,三元里,上下九……几乎跑遍了广州城。在宝华路,他刚一开唱,几十个城管就来了,他跪下陈述不幸,城管仔细听后,叫他骑上三轮车先离开,转一圈再回来。黄亚乌照办,果然城管再没干涉。
但除了岗顶、宝华路,黄亚乌在其他地方莫不遭到驱赶,在冷酷制度下,他用下跪———这种被认为最有辱男人尊严的方式也无济于事。
6月23日,他在光孝寺再遇城管,对方指着他说:“赶紧走!走!,刚开唱10分钟,城管驾到,说广州在创建文明城市,又在迎亚运,这里是一级重点监控路段,请他离开。黄亚乌笑着解释,对方礼貌而坚决地把他的小凳子往三轮车上塞:“对不起,请你理解。”
黄亚乌还是回到宝华路,城管只赶走了他对面一个卖茶杯的走鬼,但他唱到晚上7点就唱不下去了,高温下的奔波让他有些中暑。“什么叫漂泊,这种赶来赶去的滋味就是漂泊。”他说。
另两个骑着三轮车为地贫儿乞讨的家庭,湖南李顺阳,茂名电白吴碧星,面对城管时却要强硬些。前者性格比较倔强,喜欢跟城管辩理,后者有一次与城管争论,车上布条被撕掉,音响录音机被没收。
歌手江湖曾帮助李顺阳远赴长沙义演,城管不仅不驱赶,还维护场地秩序,让江湖感叹广州的冰冷。李顺阳现已为女儿筹到足够的钱,正在等待骨髓配型。吴碧星今年初差点跳珠江自杀,因为她只筹到9万多元。央视报道后,一家基金会表示愿意提供全部帮助。
江湖和九两银都曾想到,为他们帮助的地贫儿童推行规模更大的义演活动,但除了不缺志愿者,缺的只是派出所、街道、民政等相关部门的批文、公章,“没有这些就是非法活动,但拿到这些非常艰难。”
江湖说,这些家庭最困难的不是狭小三轮车上的拥挤与贫瘠,而是孤独、无助,看不到希望。除了香港、深圳少数几家地贫救济基金在帮助少数地贫儿童,官方尚未建立相关基金,医院需要高昂付费才愿治疗,而城市医保和新农村合作医疗对这种大重病的救济尚在摸索。
在看到江湖为小文炬义演的报道后,半官方组织———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启智服务总队队长李森决定施以援手。2006年5-10月,在江湖与李森策划下,一大批歌手风雨无阻,进行百场义演,最多一次获捐两万多元。
有报道说,小文炬是广州青年志愿者团队唯一以街头募捐形式救助的孩子,后来很多其他大重病孩子找到志愿者团队,但都没有获得救助。志愿者们说:“主要原因是有关部门对这种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活动没有任何批文,,属于非法组织募捐。”
2008年10月7日,4岁7个月的小文炬在南方医院接受骨髓移植手术7天后,因感染性休克、败血症等原因突然死亡。医院赔了3万元,母亲张金兰,一名头发半白的27岁女子,把筹款剩下的5万多元转交给启智服务总队,以帮助更多的人。
当晓明拉了一个晚上的肚子死去后,黄亚乌悲愤难平,但他没有像小文炬父母那样与院方理论,第二天就把晓明火化了,因为晓敏还等着救治,他还要急着去唱歌。
END
剥洋葱people
(微信号:boyangcongpeople)
记录真实可感的生命
长按或扫码关注
新京报深度报道部出品
本文发表于2009年7月15日《南方都市报》,点击阅读原文可获取原报道。
Copyright © 上海粤语新歌榜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