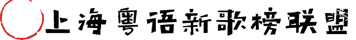导读
凸显关中文化的《白鹿原》,白描沪上世情的《繁花》,揭示中原心态的《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的地域特征显著,搬演到话剧舞台上,都用了方言。方言的“登台”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审美资源。方言的节奏、韵律以及与之相关的肢体表达,也许是方言话剧探索的方向,是话剧改变面貌的一种可能。
好像睡衣不能穿在公共场合,小龙虾上不得正式宴席,方言不知何时起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尽管生动,总似不够体面,使用方言多半意味着摹仿的是比较“坏”的人,“坏”不是指恶,而是指“丑”,指滑稽,是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的某种错误或丑陋(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五章)。戏曲中操持方言的是丑角,是雅正之外的恣肆,是端足架子之后的放松,是喜闻乐见的恶趣味,是冷场面的热调剂。方言又和喜剧小品伴生,一旦进入小品,原本并没有喜剧色彩的方言也成笑料了,东北话嚷嚷起来“你虎(傻)啊!”嚷嚷的人看起来也不精明,上海话里的“阿拉”(我)和“侬”(你)带上了娘娘腔和斤斤计较的语气处理,当“我”到了陕西成了“额”,“额”总是比较迟钝或憨傻,而山西话里的“甚事”和“作甚”都代言了“倔老西儿”,至于四川话中的“巴适”,安逸舒坦之外也有了不思进取的弦外之音。戏曲里丑角的方言往往鲜明了某种类型的缺陷,像京昆中操京白或苏白的市井小民,多油滑世故、爱占便宜;而借由电视平台面向全国播出的喜剧小品中,方言除了强化人物的类型化缺陷之外,还包含了或显或隐的地域歧视,刻板的地域印象也是方言成为笑柄的前提。再看江南地区的滑稽戏,其产生虽然和早期话剧文明戏脱不了干系,但其娘胎是方言,尤其是江、浙、沪的方言,其源起是归入曲艺类别的独角戏,所以滑稽戏虽然没有自己的唱腔,也还是划分在了戏曲的范畴。
▲陕西人艺《白鹿原》演出剧照 图片来源网络
方言就此和话剧楚河汉界了,一个是本土的,一个是舶来的,一个是家常饭菜,一个是西式大餐,一个和曲艺、戏曲是一家人,而另一个和交响乐、芭蕾是亲戚,前者尽可以熟不拘礼,后者则要求正襟危坐。西方话剧的文本中当然也少不了俚语和土话,,但一经国内的翻译和表演,还是带着洋范儿,隔阂着观众。一个多世纪之前,有志之士们迎接话剧的到来,是有意屏蔽甚至是故意针对戏曲和曲艺的,戏曲和曲艺的内容、形式、格调乃至班社的组织、师徒的教习、演出的规矩都不入话剧追随者们的法眼,来自外邦的话剧简直像来苏药水消过毒的,散发着文明与科学的气息,担负着启蒙的重任,与原生的和旧日的一切都毫无关系,更别说与方言有染了。曲艺、地方戏曲和方言水乳交融,即便是唱词,也像口语的大白话,话剧则不然,即便是对白,也有一定的书面语言特征。演外国戏自是不必说了,曹禺先生的《雷雨》或《日出》也很难想象用天津话演出,他改编的巴金先生的《家》,觉新、瑞珏乃至鸣凤等也不像说四川话的,只有陈姨太和冯乐山适合用方言处理?那又是漫画式的丑角了。话剧由翻译文本引进到中国,好像“母语”天然地就是普通话,普通话不仅是表达工具,更是进入了思维的,连话剧的主题和人物也都是经普通话“改造”过的,有着和生活在方言世界中的百姓不大一样的面貌。话剧和普通话画了等号,和进步画了等号,和新文艺及新文艺工作者之间画了等号,和民众优越地拉开了距离。
然而,骄傲的话剧打摆子似的热一阵冷一阵,至今还水土不服。回顾曾经红火过的喜剧小品,是曲艺和戏曲借鉴了话剧,也是话剧向曲艺和戏曲的妥协,方言的运用正是其中的一项表征。这两年,陕西人艺版的《白鹿原》满台的陕西话、四川人艺版的《茶馆》讲四川话,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和上海五盟文化联合出品的《繁花》用上海话演出,北京鼓楼西剧场领衔制作的《一句顶一万句》则用了河南话。不约而同,一时间方言纷纷登上话剧舞台,是话剧的自觉还是自救呢?
方言话剧并不新鲜,在北京人艺,1984年林兆华导演的《红白喜事》(编剧魏敏、孟冰、李冬青、林郎)用了河北方言,2006年同样由林兆华执导的《白鹿原》(编剧孟冰)用的是陕西方言。1990年查丽芳在四川成都话剧团导演的《死水微澜》(编剧查丽芳)是四川方言版的,2006年王小琮在陕西西安话剧团导演的《郭双印连他乡党》(编剧王真)是陕西方言版的,当时的报道称之为“原生态方言话剧”,更具体地说,剧中用的是陕西西府话,面对遭到的异议,王小琮导演的回应是,中国话剧走向本土化、方言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著名编剧曹路生多年来一直倡导沪语话剧,由他改编的《永远的尹雪艳》在构思当初就决定用上海话写成剧本。而在香港,“粤语话剧”天经地义。翻看香港话剧团驻团编剧杜国威的剧作集,句式、称呼、语气词,所有的语言习惯都是粤语的,猛然间还有些看不懂。
粤语话剧除外,曾经的方言话剧偶尔惊艳,没有形成气候。陕西方言版《白鹿原》、沪语版《繁花》和河南话版《一句顶一万句》的出现,会推动方言话剧的发展吗?最低限度,这些剧目再度确认了方言是一种审美资源。
没有什么比方言更能代表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的精神面貌了,白家、鹿家的大家长不讲关中方言了,是否少了族长威严?信奉儒家的朱先生不讲关中方言了,是否少了乡间儒者的神韵?小娥不讲关中方言了,女子的明艳和不幸都打了折扣?在建都镐京(今西安市东南部)的西周,关中方言称为“雅言”,受到周王朝的全力推广。近三千年过去,现存的关中方言早已不再是国家正音,经过了数个朝代的更迭也与西周时的语音语调相去甚远,但仍留存了部分古汉语的语言习惯,当地人宣称,《诗经》用关中方言诵读最朗朗上口、传神动听。关中方言的古拙赋予了话剧《白鹿原》厚重感,像是历史在发声,先人在讲话,石头似的碾压过来,和黑灰暗哑的舞台主色调相匹配,几欲令人窒息。
《繁花》的情形有趣,在上海演出时,台上的沪语和剧院前厅精心放置的上海老物件、为观众提供的麦乳精一并构成了怀旧的语境。对上海的怀旧似乎是上世纪90年代由台湾人始作俑的,上海已经暗淡很久了,努力洗去“冒险家乐园”的称号,努力与资产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是彻底从了良的,改革开放之后,眼看着广东和特区抢了风头,也还是小心翼翼地本分着。倒是台湾人,包租了百乐门舞厅、颜料大王吴同文的旧居“绿房子”重新装修,不落忍风华绝代的上海竟落寞和没落。台湾人对上海的怀旧,是钟情于上海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怀恋张爱玲和新感觉派的上海,是缅怀一个失去了的旧梦和传奇。《繁花》不同,《繁花》是上海人的上海,是文学中隐遁了的1949年之后的大半个世纪的上海,是不曾被书写过的上海,这一页才刚刚翻过,音容宛在,贴心贴肺。沪语,是上海和它的儿女们的呢呢喃喃,与旁人不搭界。上海观众看《繁花》就是看自己,至多是瞄到隔壁头邻居,都是屋里厢事体,而《繁花》一旦亮相外地,上海和沪语都成了消费对象,沪语是外人窥视上海的小孔,探秘上海的路径。上海特殊,话剧《繁花》采用沪语,从市场的角度是双赢。
于《一句顶一万句》,方言已经成了一种策略。排练之前,微信推送招募河南籍讲河南方言的演员,既是广告又是宣传,先声夺人。与之关联的,是对出现在电视媒体频率最高的河南籍作家刘震云的IP分享,也是对久无新作问世的先锋导演牟森的一次创作想象。舞台上的《一句顶一万句》其实不仅有河南话,还依照小说原作对人物的规定讲了山西话和东北话,但毫无疑问,籍贯河南的作家刘震云写河南延津县的作品用河南演员说河南话演,这是一个噱头,而且因为导演是牟森,这并不先锋的做法好像有可能“先锋”了。首演前,刘震云带领五十余位读者在长城脚下朗读剧本片段,在媒体见面会上,他称牟森“开创了新的话剧形式,让几个河南人对世界说一点自己的心事”,“河南人”“说”成了这个戏的招牌。
▲《一句顶一万句》演出剧照 图片来源网络
方言就是身份!是文化身份、地域身份也是个人身份,是自身身份的在场,也是对他人身份的想象,是深切的自我体察,也是异化和猎奇的对象。与早些年的方言话剧不同,《白鹿原》《繁花》《一句顶一万句》等剧目的问世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即方言的衰落。在不少城市,方言几近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到了幼儿园要把方言儿歌纳入教学计划的地步,难道上了戏台的都濒危?还是濒危的都上了戏台?当方言成了审美资源和艺术手段,它与日常是更紧密了还是更割裂了?这些戏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改编自小说,小说作者写的都是故土,而导演都是外乡人。作家下笔时,叙述的语感是含着方言特质的,导演二度创作时,因其不是自己的方言而更依赖和强调了方言。
从这个角度看,老舍先生的剧作直接关乎北京人艺演剧风格的创立,方言也是一大因素,北京话亦是方言。方言等同于地域,因此,四川省人艺的川版《茶馆》难的不是四川话,而是四川“化”,四川也有茶馆和茶馆文化,但四川的茶馆和茶馆文化与北京的一样吗?四川茶馆里头的掌柜和茶客,脾气秉性与裕泰茶馆的一样吗?应付时代变迁,川人有川人的智慧。老舍先生的《茶馆》如果很方便地能转化成川版、粤版、湘版、鄂版……恐怕是老舍先生的失败。方言移植不易,也不易移植,各地的话剧团都至少该有一两部自己方言的话剧代表作,都该向粤语话剧学习,编剧们下笔时也该进入方言语境,进入地域文化。
《白鹿原》《繁花》《一句顶一万句》,以及前辈的《死水微澜》,小说本身并不是用方言写的,不像吴语写作的《海上花》,还劳张爱玲翻译了一遍。关中、沪上、中原或巴蜀的方言是这些小说的语境,孕育了这些小说的语感,搬演上舞台时,各具特色的地方方言是语境和语感的直接体现。方言既然成了手段和语汇,方言话剧中“异质”的普通话也要在手段和语汇的层面纳入考量了。
沪语话剧《繁花》中,有位北面来的李李小姐,从头到尾讲的就是普通话。话剧的改编照搬了小说,李小姐开餐馆,是个善于经营的老板娘,风情万种又自知分寸,青睐她的男人不少,她独独对阿宝动了心思,告诉了阿宝她的故事。和小说中描写其他沪上各个阶层、各个时代男女的恋爱、调情、欲望不一样,李李的经历有点儿像早些年地摊文学中常见的:她是到处接活的“野模”,被骗去澳门做不穿内衣的表演,因不从受到了更大侮辱,昏迷后小腹遭文身,直至逃脱出来,“上岸”重新开始生活,格外的自我保护。她是反传奇的《繁花》中的传奇,她的出身是北方的,她噩梦般的遭遇是在南方的,她极好地适应和镶嵌在上海的规则里,让封闭了很久重新打开的上海既爱又怕。小说中,李李的这一笔算不上精彩,甚至有些突兀;舞台上,李李的不堪过往全是倾诉,她是讲给阿宝听,但台上的阿宝是“不响”的,,她的讲述成了长长的一段独白。这场戏受到的批评和异议最多,与全剧最不协调,小说中已有的格格不入在舞台上愈加放大了,很大程度是源于李李那口标准的普通话。《繁花》好在是“繁”“花”,枝枝蔓蔓密密匝匝,清晰明确的吐字归音让李李像一片繁花中的一枝罂粟,破坏了“繁花”的景致。
▲《繁花》演出剧照 图片来源网络
方言版《一句顶一万句》中,歌队唱的是普通话。没错,歌队是真的在歌唱,歌唱的是小说中的语句,多用于交代时间、地点和情节发展,有时也揭示人物心理活动,唱的全然是“宣叙调”,是陈述而非中文语境中的“歌词”,和满台的河南话、山西话并置,有点儿怪诞。在《一句顶一万句》以及刘震云的不少作品包括新作《吃瓜群众的儿女们》中,“这件事”总是不知不觉变成了“那件事”,凡事都经不起人心的“弯弯绕”,驴唇就是能对上马嘴!事情不重要,可堪同情的外在际遇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夹杂着农民狡黠、民间智慧和愚昧自私的集体无意识,让种种不可思议运转得天衣无缝,生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最后令人不得不对熟透了的中原文化无奈喟叹。所谓“现实魔幻主义”,现实之所以魔幻,是生存的文化环境、心理环境的丑陋,是农耕民族小农意识的局限。牟森导演反复强调,他认为《一句顶一万句》是平民史诗,小说原作是否“史诗”,各人有各人的解读,但“史诗”决定了牟森导演的“史诗体”(叙述体),叙述者曹青娥和歌队都来了,上半场说河南话的杨百顺们和下半场说山西话的牛建国们由“宣叙调”连缀着。普通话歌咏的宣叙调一本正经,普通话的官方和权威色彩与其歌唱的内容形成反差,与杨百顺、牛建国们的遭遇八竿子打不着,像是把野史正史化了,让民间的、个体的、稗官的进入宏大叙事了,让“宏大”徒有其表虚张声势了,让个人的遭遇荒诞不经了。歌队是孟京辉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法宝也耍宝似的一件利器,有歌队便有戏谑,也验证在牟森的《一句顶一万句》中。
都是用方言,同一种方言用在不同人物身上,效果也是不同的。在为方言“正名”的方言话剧中,方言有时还会像戏曲丑角的白口一般,服务于喜剧性。
比如《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洋牧师老詹,万里迢迢地从意大利教廷来到河南延津,传教大半生也没有发展出虔诚的教徒,苦心营造的教堂还给新来的县官征用了做学堂,一个失败的上帝的牧羊人。偏偏他也讲河南话,用土话宣讲洋教,洋教变了味儿,错位造成了滑稽感。
再比如《繁花》中的大妹妹和兰兰,两个“女小人”一早出场,互不相让地斗嘴,,担心前途命运。两个上海小姑娘自然都是讲上海话的,但她们台词的内容只是再一次印证和加深了人们对上海女孩的固有印象,娇气、爱漂亮,还有那么一点儿肤浅。大妹妹和兰兰的出现总是引起笑声,但在小说中,不是这样的。小说里写大妹妹和兰兰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游荡在南京路上,暗自算着有多少男青年想接近她们,看似无聊实则无助,有青春期青春总是无处安放的彷徨,有大背景下个人无从掌握方向的放弃,日子总是要荒废下去的,她们越是沉浸在这游戏,越是令人唏嘘。舞台剧中显然把大妹妹和兰兰当成了女丑般的色彩人物,作用于结构的完整而不刻画她们自身,如此一来,少了原作对她们的体恤和慈悲,也显示出改编者们力求让戏好看的意图。有时,增色或减分的地方并不在于对主要人物、必需场面的处理,恰恰是在大妹妹和兰兰这样的小角色身上,流露出主创在诗意的日常性与可看的戏剧性之间的选择。沪语版《繁花》还是倾向于“有戏”、倾向于剧场效果,在大妹妹和兰兰这组人物上可见一斑。
在方言话剧中处理方言的分寸,比索性让丑角讲方言更微妙。
方言演话剧,好像和它的洋出身远了,和戏曲、曲艺近了。《郭双印连他乡党》中,唱了一段秦腔,自然而然;观看陕西人艺的《白鹿原》时,本地演员们的关中方言充满节奏和韵律感,竟不时感到可以起势唱起来了!原来方言的腔调真的能产生唱腔。也许是这个原因,粤语话剧中唱起粤语歌来十分自然,而根植于地域小说的改编也往往除了话剧之外还有戏曲和曲艺的形式,像李劼人先生的《死水微澜》改编成了川剧,金宇澄先生的《繁花》改编成了评弹,老舍先生的作品更是催生了北京曲剧。
▲四川人艺《茶馆》演出剧照 图片来源网络
方言话剧中也的确有戏曲演员的登台。都是讲河南话,《一句顶一万句》中豫剧演员的台词是豫剧道白式的,身段接近豫剧现代戏,有程式动作的影子,表演自带锣鼓点。她们带着戏曲表演的痕迹,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发挥戏曲表演。当语言方式从普通话改为方言了,表演要不要随之变化?肢体的运动节奏会不会随之变化?于《繁花》,影视式的生活化的表演是恰当的,但《一句顶一万句》是否有别的可能?是否可以尝试用更多的戏曲手段、让戏曲手段脱离原来的表现内容“错置”在话剧舞台上,更加放大刘震云小说中的荒诞不经?把戏曲演员只当作话剧演员用,可惜了;方言话剧只停留在用方言演话剧,更可惜了。
方言话剧是话剧的自觉,也是话剧的自救。方言演话剧不是话剧的必须和全部,但一定是话剧探索的一条途径,语言方式的改变,改变的岂止语言?
(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18年9月总第二十六期)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禁止转载,转载合作请联系后台)
作者简介
郭晨子: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